你所在的街道,为什么叫现在这个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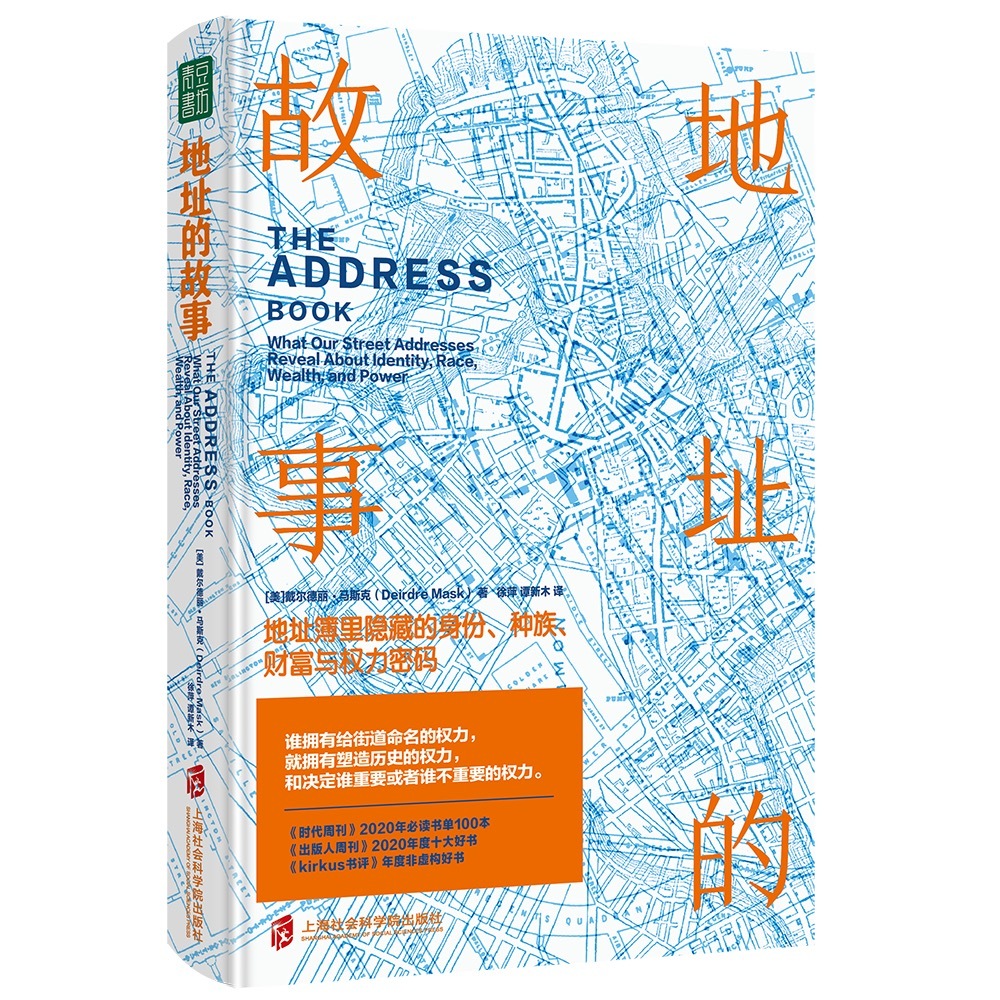
【编者按】上海新一轮疫情防控管理落实以来,“街道”一词频频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可能也是因为这段特殊时期,很多市民知道了原来上海16区里有107个街道,也有人开始对自己所处的街道有了更多认知,知晓了它准确的名字。
世界各地的街道命名都是一门学问,比如给单个房屋编上号码的做法始于18世纪的维也纳;19世纪的伦敦,约翰·斯诺博士利用该市刚创造的房屋编号查明了一次霍乱流行的来源和传播路线;有的城市的街道甚至没有名字……在近期出版的《地址的故事》中,美国学者戴尔德丽·马斯克(Deirdre Mask)就为读者讲述了全球城市街道的故事,它们诉说着城市的历史隐藏在地址中的历史,揭示了街道名称、房屋编号怎样与人们的身份、阶层、种族有关,还有更深层的为什么它们关系到命名的权力、隐瞒的权力并且决定谁重要谁不重要的权力,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经出版社授权,摘取书中讲述日本和韩国街道的精彩篇章,一起来看看“没有被命名过”的街道及其神奇的地址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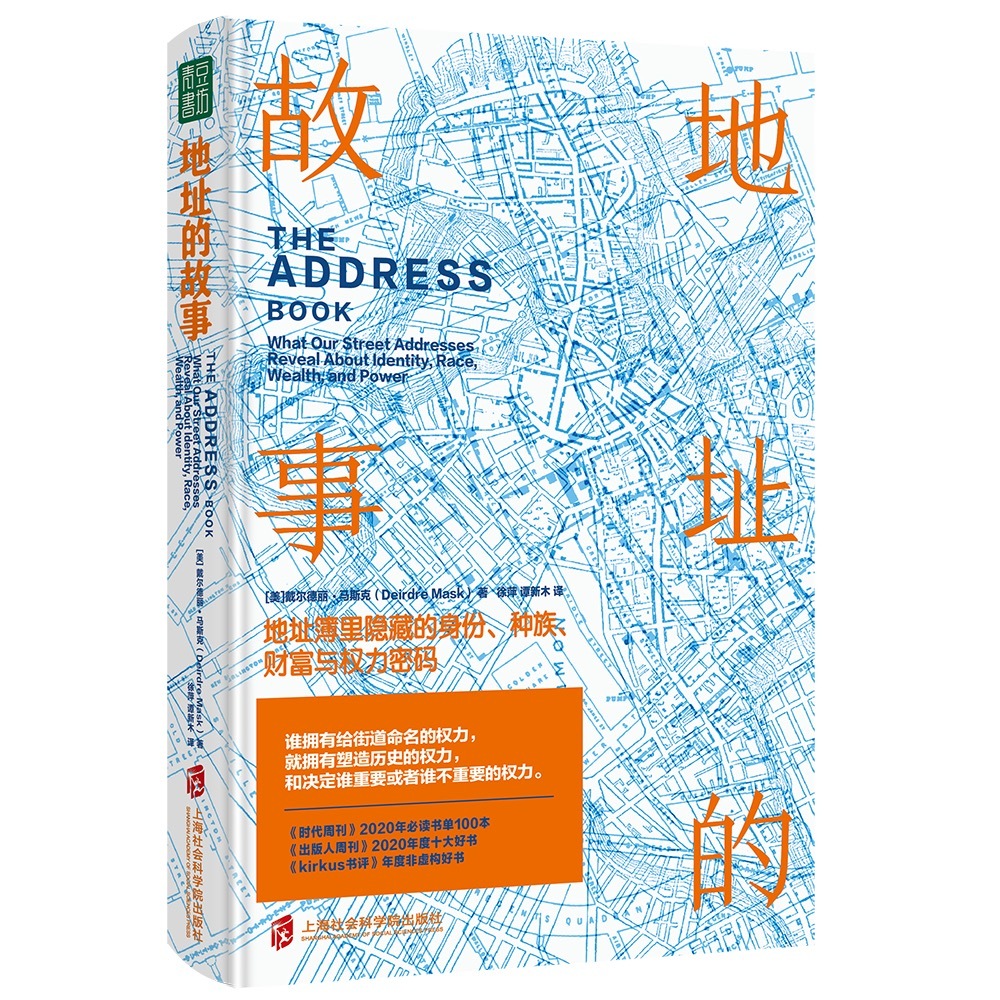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徐萍谭新木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青豆书坊,2022年1月“这座城市的街道没有名字。”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这样描述他在东京的时光。1966年春,巴特应邀到日本讲学, 主题是“叙事的结构分析”。这次讲学只是去东京的借口,他五十多岁,已经在法国成名,法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学理论家可以出名的国家。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解释的那样,他到日本旅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自己身为法国人的巨大责任”。
东京与巴黎的大相径庭使巴特兴奋不已。他写道:“生活在一个不懂语言的国家,大胆地生活在旅游线路之外,无拘无束地生活,是最 危险的冒险。”如果“我不得不构思一个新的《鲁滨逊漂流记》,我不会把鲁滨逊放在一个荒岛上,而是要放在一个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里,在那里,他既不懂得当地的语言,也不能阅读当地的文字:我认为,这将是笛福故事的现代版本。”
成为鲁滨逊·克鲁索,甚至只是迷失在异国的城市,在我听来都很悲惨。但巴特是一位符号学家,这意味着他在一切事物中寻找意义。(如果有人指责你对事物的解读过多,那么你自己可能就是符号学家。)在日本这样的地方,一切似乎都是那么不同,巴特完全摆脱了以往理解能力的束缚。亚当·沙茨在《纽约书评》上写道:“没有什么比他不懂的语言的‘叽里咕噜声’更让他高兴的了。”“语言终于从意义中解放出来,从他称之为‘黏性’的指称属性中解放出来,并转化为纯粹的声音。”回到法国, 巴特对日本产生了想家的感觉。几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路标帝国》,其中的某些部分描述了他在东京街头旅行的经历。
《路标帝国》英文版今天,在巴特第一次日本之行50多年后,东京也许没有什么比缺乏街道名称更能激怒西方游客了。(只有少数主要街道被命名)东京没有给街道命名,而是对街区进行编号。街道只是街区之间的空间。东京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地理顺序编号,而是按建造的时间编号的。街道名称的缺失,使得导航变得困难,即使对来自日本国内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路,东京到处都是“警察岗亭”,那是非常小型的建筑,配备了熟悉这一地区的警察,还有详细的地图和厚厚的目录。
东京上野公园警察岗亭传真机在日本经久不衰,尽管它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很久了,部分原因是——为了,而且绝对必要——发送地图。巴特自己写道,有时他会让出租车司机去一个红色的大电话亭打电话给主人问路。智能手机地图给东京的出行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手绘地图是巴特在日本时期的乐趣之一。他说:“看别人写字总是令人愉快的,更何况看别人画画。”“每次有人这样给我指路,我都会记住谈话者的姿势,他们把铅笔倒过来,用另一端的橡皮,擦掉多画出来的弯弯曲曲的大路以及高架桥的路口。”
哈佛大学日本历史教授大卫·豪厄尔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解释道,在日本历史上,街道从来没有被命名过。17世纪的城市社区被分割成矩形街区,拥有该街区财产的人对其治理负有一定责任。该街区成为城市管理和地理的关键单元,一组街区常常共用一个名字。大多数社区都有一家商店,新来的人可以在那里问路。武士们住在一个有围墙且面积较大的院落里,只需要通过询问就能很容易地找到这些位置,或者使用市面上流传的众多地图中的一张就能找到。 豪厄尔告诉我:“人们似乎觉得没必要将不变的标识符固定在地块或结构上。”“我想是因为这些街区很小,很容易找到东西。”地块编号是在后来被加上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街区又被细分为了几个街区。日本人似乎从来没有理由改变这种做法。
日本街区标识板这种历史性的解释使我懂得了日本的地址系统是如何形成的,但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一开始就认为街区是一种组织空间的有效方式。如今居住在日本的城市设计教授巴里·谢尔顿发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他在战后英国的一个小城市作为小学生的学习经历。谢尔顿在诺丁汉长大,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给他一叠画了线条的纸,教他写字母表。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沿着直线,整齐地书写字母,有时“甚至有额外的线条用于写小写字母的头部和尾巴”,这也是我在美国学习拼写的方式,也是我五岁的孩子今天的学习方式。
但是当谢尔顿发现他的妻子百代子是如何学会写字的时候, 他感到很惊讶。百代子来自日本,她的书写纸和我、和谢尔顿记忆中的纸完全不一样。日语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但大部分书面日语使用汉字,即从汉语中借来的汉字。汉字是表形文字——每个字符代表一个词或意义。尽管汉字的形状可能为理解它的含义提 供了线索,但大多数情况下,汉字的写法只需记住;它们不能“通过发音拼写出来”。 汉字不是写在线条的纸张上的。相反,百代子告诉巴里,在日本,他们的写字纸张没有线条,只有几十个方块区域。(这种纸张被称为“原稿用纸”,至今仍在日本学校使用)每一个汉字都是独立的;每一个汉字都完全可以独立理解,不像英文字母,除非把它们排成一行,从左到右读组成单词,否则没有意义。(英语单词也必须有适当的间距——“red one”与“redone”完全不同。)即使用英语读所有的大写字母也很累人,而读几个垂直书写的单词是很痛苦的。但日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轻松阅读。巴特指出,羽毛笔只可以“朝一个方向书写”,但日本毛笔可以随心所欲地朝任何方向书写。 谢尔顿是一位城市设计专家,他开始将书写系统的差异与西方人和日本人看待城市的方式联系起来。谢尔顿认为,那些学会用英语写作的人,都受过看线条的训练。所以西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街道——线条——坚持给它们命名。但在日本,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言,街道本身“在日本的城市规划中似乎意义太小,无法保证名字所赋予的意义”。谢尔顿的理论认为,日本人关注的是区域或街区。
东京银座地图谢尔顿后来在一本比较烧脑的书籍《向日本城市学习》中写道:“我将回忆起当时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让我大吃一惊,但却提供了一些持久的启发。”“一位日本老人给我画了一张地图,上面显示了他在复杂地形上分散的、形状和大小各异的土地。他先画了一些分散的地块(住宅地块首先从他明显的个人参照点开始绘制),然后他开始通过道路和小径将它们连接起来。”在他看来,这些建筑与它们所在的街道没有联系。“我能说的是,”谢尔顿补充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西方人能够画一幅这样的地图, 他们总是先画出街道和道路——线条。”
东京地标之一,涩谷站Japan guide 图这些差异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并不总是能够欣赏东京城市景观的美丽。当谢尔顿第一次来到东京时,他对东京感到“困惑、恼怒,甚至害怕”。东京之所以让他迷失方向,是因为它的设计与西方迥然不同。谢尔顿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游客们长期以来一直感叹,东京似乎是没有计划的,没有主要的公园、广场或景致。
住在东京的记者彼得·波波姆曾表示,东京看起来像是一个“毫无秩序的混凝土丛林”。
东京 Japan guide 图波波姆接着说,如果只在这种视野下观看东京,那就无法看到这座城市的全貌。人们在纽约和巴黎等城市习惯的那种综合性规划,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概念。波波姆解释说,这种整合是“日本人并不期待的一种美”,相反,日本人“迷恋城市中特定的建筑和空间,迷恋它们展示出来的沉着、风度、机智或魅力,但是他们每次可能迷恋不同的建筑和空间。”在这座城市中行走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巴特深情地写道,在东京,你“不能通过书本和地址来导航,而是通过走路、视力、习惯、经验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只有记住了这些,你才能重复同样的旅程。
“第一次造访一个地方”,他写道,“就意味着开始描绘它,不是书写, 而是必须建立起对这个地方的独特描绘方式。”
日本不是唯一使用块状街区作为地址编制基本单位的国家。2011年之前,韩国有一套类似日本的系统,一些街道,特别是主要街道都有名字,但其他街道的地址系统都是围绕街区组织的。 这套系统制度很可能是从日本引进的,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 在“二战”中战败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直将朝鲜作为“保护国”统治。
韩国旧的地址系统韩国人有一个类似英语的字母表,但是他们像日语一样写方块字。这能用来解释他们的街道地址吗?66年来,韩国一直保留着日本的街区寻址系统。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个地址系统是殖民时期形成的,
2011年,政府宣布改变韩国的地址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国开始采用更为西式的街道命名和房屋编号方法。
新的地址系统政府大力推广新的地址系统,向那些通过
在线系统转换街道地址
的人发放蓝牙耳机。如果人们改用新系统,电视购物公司就会提供10美元的礼券,忠清北道省给有孩子的家庭发放刻有新街道地址的手镯。
韩国官方设立在线系统转换街道地址网站 英文版截图但每一个和我闲谈的韩国人都说,他们并没有真正使用它们。出租车司机和邮递员一样把新地址转换回旧系统。当然,这种不情愿可能是暂时的,在下一代人成长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其他解决街道问题的方法。或者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韩国人仍在通过街区来阅读他们的城市。
